转载文章-器官移植 itranspl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
执笔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窦科峰、陶开山、张玄、宋俊伯)通信作者:窦科峰,Email:doukef@fmmu.edu.cn;陶开山,Email:taokaishan0686@163.com

通信作者:窦科峰,肝胆外科、器官移植学家,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一级教授、空军专业技术少将,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全军普通外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普通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长期致力于复杂肝胆胰疾病的临床诊治和器官移植研究工作。完成国内首例成功的活体肝移植、亚洲首例成功的肝胰肾联合移植、亚洲首例心肝肾联合移植。国际首创脾窝辅助性肝移植术。完成国内首例基因编辑猪-猴异种肝移植、国际首例基因编辑猪-脑死亡受体肝移植等开创性工作。
主持国家973、173、863计划等课题30余项,发表论文670余篇,其中SCI论文180余篇,单篇最高他引1600余次。主编专著9部。领衔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以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师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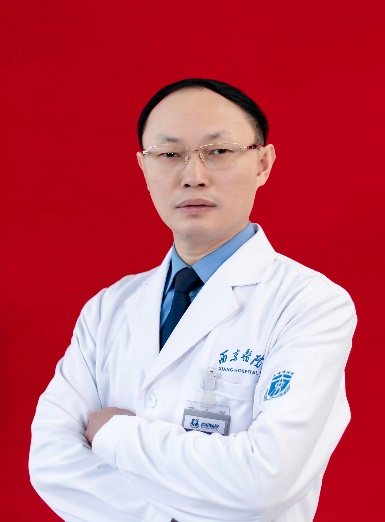
通信作者:陶开山,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普通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脏外科专家工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门脉高压症专家工作组副组长、全军器官移植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等职。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军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30余项课题研究。牵头获陕西省“三秦学者”器官移植全国一流创新团队。共发表论著18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国外发表SCI论著100余篇。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8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1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次、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
摘 要
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是利用脑死亡受者进行的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是异种器官移植从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逐步走向临床应用的重要中间环节,为异种移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为推进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安全有序、科学规范的开展,根据相关法律和规范,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从供体猪的选择、受者的选择标准、法律法规及伦理要求、试验终止时间的确定、家属知情同意制度、脑死亡判定标准等方面,制定了《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专家共识(2024版)》。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但长期以来,可用的人类供器官数量严重不足,导致许多患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异种器官移植即将猪等动物的器官移植到人类患者体内,为长远解决器官短缺这一问题提供了潜在的方案[1]。猪因其生理特性与人类相似,被认为是理想的供体动物。随着基因修饰技术如CRISPR-Cas9的应用,对供体猪进行精确的基因修饰已成为可能,这为提高异种器官与人类受者之间的免疫兼容性提供了新的策略[2]。然而,异种移植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免疫排斥反应、跨物种病原体传播风险、伦理和法律问题。因此,使用脑死亡受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异种移植研究,为评估移植器官的功能性和围手术期治疗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受者选择、知情同意和脑死亡判定标准等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3]。本专家共识旨在综合当前异种器官移植的科学研究、伦理考量、法律法规要求以及临床实践经验,为脑死亡受者中的猪肝脏、肾脏、心脏移植提供指导。探讨供体猪的选择、受者的选择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及伦理要求、试验终止时间的选择、家属知情权以及脑死亡判定标准等问题,以期为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供体猪的选择
在异种器官移植领域,供体猪的选择对于确保移植成功和受体安全至关重要。供体猪的基因修饰技术进步,特别是CRISPR-Cas9的应用,已经使得精确修改猪基因组以提高与人类受者的免疫兼容性成为可能,如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α-1, 3-galactosyltransferase,GGTA1)基因敲除,以及引入人类补体、凝血调节蛋白等[4],这些基因修饰旨在减少或消除导致超急性和急性排斥反应的异种抗原,以及增加移植物生理功能调节的兼容性问题。
1.1 基因修饰策略
因修饰技术在异种器官移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允许科学家对供体猪的基因组进行精确的修改,以提高其器官与人类受者的兼容性。目前,异种移植领域中已有多种关键的基因修饰策略被用于异种移植实践,或正处在研究中,以期改善异种移植的结果。
1.1.1 α-1,3-半乳糖基转移酶基因敲除
猪是α-1,3-半乳糖(α-1,3-galactose,αGal)抗原的主要来源,这是引起人类对猪器官产生超急性排斥反应的关键因子。通过CRISPR-Cas9技术敲除猪的GGTA1基因,可以显著降低这种排斥反应的风险。此外,β-1,4-N-乙酰半乳糖氨基转移酶2(β-1,4-N-acetyl-galactosaminyltransferase 2,β4GALNT2)、单磷酸胞嘧啶-N-乙酰神经氨酸羟化酶(cytidine monophospho-N-acetylneuraminic acid hydroxylase,CMAH)基因的敲除对于降低亚临床试验中的急性体液性排斥反应也非常重要。GGTA1/β4GalNT2/CMAH三基因敲除猪已被用于多项研究,证明了其在减少异种器官移植超急性排斥反应方面的潜力[5]。
1.1.2 人类补体调节蛋白的表达
补体系统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在异种移植中引起的急性体液性排斥反应和炎症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基因修饰技术,可以使猪的器官表达人类的补体调节蛋白,如人类衰变加速因子(human decay-accelerating factor,hDAF,即hCD55)、人类膜辅助因子(hCD46)和人类膜攻击复合物抑制因子(hCD59),将有助于保护移植的器官免受补体介导的损伤[6]。
1.1.3 抗凝血和抗炎因子
为了进一步减少异种移植中的凝血和炎症反应,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在猪的基因组中插入抗凝血和抗炎因子。如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TFPI)和CD39的转基因表达已被证明可以减少异种移植物中的凝血和炎症[7]。此外,人内皮蛋白C受体(human endothelial protein C receptor,hEPCR)也是抑制凝血发生的蛋白,过表达这3个蛋白可有效抑制血栓形成,同时可以减轻移植后的炎症反应。
1.1.4 细胞保护因子
细胞保护因子如血红素加氧酶(heme oxygenase,HO)-1和A20,可以在移植过程中为细胞提供保护,抵抗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基因的转入可以提高异种移植物的存活率[8]。
1.1.5 多基因修饰策略
随着基因修饰技术的进步,目前可以在猪的基因组中同时进行多个基因的修饰。这种多基因组合修饰策略允许研究人员同时解决异种移植中的多个障碍,从而提高移植的成功率[9]。现阶段进行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的供体猪基因修饰方案需要满足至少三种主要异种抗原敲除、两种人类补体调节蛋白和一种凝血调节蛋白转入。在此基础上,可适当转入抗炎、抗吞噬蛋白。
1.2 供体猪的大小和生理特性
供体猪的生理特性对于确保异种器官移植的成功至关重要。选择合适的供体猪不仅涉及到器官的大小和功能,还包括了对供体猪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生理状态的综合考量。
首先,供体猪的器官大小需要与人类器官相匹配,这是移植器官能够在受者内正常发挥功能的前提,而过大或过小的器官都可能导致移植后的并发症,影响移植效果[5]。供体猪的生理功能也是选择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猪的代谢率、心率和血压等生理参数应尽可能接近人类,以减少移植后由于生理不匹配导致的功能障碍。此外,猪的生长发育阶段也很重要,因为不同年龄的猪器官成熟度和功能状态存在差异,如成人异种心脏移植采用60 kg左右的供体猪较为合适,而成人异种全肝移植采用10月龄供体猪(肝重约1 000 g)较为合适。同时,供体猪必须经过严格的健康筛查,确保没有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以避免将疾病传播给人类受者。这包括移植前对猪进行血液和组织检查,以及对可能的病原体进行检测,如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orcine endogenous retroviruses,PERV)、猪巨细胞病毒(porcine cytomegalovirus,PCMV)和其他潜在的微生物感染。研究表明,PCMV的感染状态和异种移植物的排斥反应直接相关。此外,供体猪的基因背景对其器官的质量和移植后的长期存活率也有重要影响。特定的遗传特性可能与移植后的免疫反应和排斥风险有关。因此,选择遗传背景清晰、健康状况良好的供体猪对提高移植成功率至关重要。
1.3 无指定病原体状态
供体猪的无指定病原体(designated pathogen free,DPF)状态是异种器官移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确保了供体猪在没有指定病原体的环境中生长,从而降低了将病原体传播给人类受者的风险。DPF状态的实现涉及多个方面的严格控制和监测。为了建立和维护DPF环境,必须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这包括对供体猪进行隔离饲养、提供无菌饲料以及对其生活环境进行定期的病原体检测。此外,还需要对饲养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他们了解并遵守DPF设施的操作规程[10]。
此外,DPF猪需要接受一系列病原体筛查,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微生物。这些筛查通常包括血清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和病毒分离实验。定期监测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控制潜在的病原体感染,从而保证供体猪的健康状况[11]。同时,DPF猪的免疫状态需要进行控制,以确保它们在不受到病原体攻击的同时,仍能保持一定的免疫能力。这可能涉及到对供体猪进行特定的疫苗接种计划[12]。
总之,维持DPF状态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持续的投入。这包括对设施、人员、饲养程序和监测系统的定期审查和更新,以应对新出现的病原体[13]。通过实现和维护DPF状态,可以显著提高异种器官移植的安全性,为患者提供更安全的供体器官,从而有望挽救更多生命。
1.4 动物伦理和法律要求
在异种器官移植领域,供体猪的选择和使用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和法律标准,这些标准旨在确保动物福利、研究伦理以及人类受者的安全。
伦理审查是进行动物研究的前提条件。所有涉及动物的研究方案,包括供体猪的饲养和使用,都必须经过独立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这些委员会将评估研究的必要性、动物使用的数量和方式,以及是否采取了减少动物痛苦和压力的措施。此外,伦理审查还包括对研究目的、设计和潜在的人类受益的考量,确保研究的正当性[14]。
动物福利是另一个核心问题。供体猪的饲养和管理应遵循高标准的动物福利准则,包括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营养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水以及必要的医疗护理。此外,应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和实验操作,确保供体猪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尊重和善待[15]。
2. 受者的选择标准
在选择脑死亡受者进行异种移植试验时,选择合适的受者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到生理状态、免疫状态、社会支持水平等多个方面。
2.1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主要考虑受者的生理条件。包括:(1)受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脑死亡确认流程,这一状态需由独立的医疗团队根据国际指南进行确认[16];(2)心血管系统的稳定性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受者需要有稳定的血压(收缩压90~140 mmHg,舒张压60~90 mmHg,1 mmHg=0.133kPa)和心率(60~100次/分),以保证移植物的血液供应[17];(3)内环境的稳定性也是选择受者时必须考虑的,包括电解质平衡、血糖水平和血液酸碱状态,这些因素共同反映了受者的总体生理状况;(4)凝血功能的评估同样重要,因为凝血功能异常可能导致手术过程中的出血风险增加;(5)受者的解剖结构应适合手术,以确保移植器官可以正确安置并发挥功能;(6)需对受者进行传染病筛查,以确保没有活动性或潜在的传染病,这不仅影响受者的安全,也可能对研究团队构成威胁;(7)年龄也是选择受者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推荐年龄18~70岁,性别不限,除脑死亡外,受者其它器官能够耐受移植手术创伤;(8)评估受者对免疫抑制药的反应也很重要,这有助于预测移植后可能的药物反应并提前调整治疗方案。
2.2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旨在避免将高风险受者纳入研究。包括:(1)对猪组织有已知过敏史的受者,由于可能发生严重的免疫反应,应被排除在异种移植之外;(2)患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等免疫功能障碍者;(3)患有重要器官重度感染的受者,由于感染可能在移植后加剧,并且可能影响移植器官,因此也应被排除[18];(4)确诊系统性免疫疾病或应用免疫抑制药,影响全身免疫功能者;(5)恶性肿瘤患者由于免疫抑制治疗可能促进肿瘤发展,同样不适合接受异种移植[4];(6)既往接受异种或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者;(7)因宗教信仰、民族等问题不能接受猪源性材料者;(8)入组前3个月内参加过其他药物临床研究者。
值得注意的是,脑死亡后常见的生理紊乱,如激素失调、低体温和轻度肺水肿等,则不应被视为排除标准[19]。
2.3 免疫状态评估
免疫状态评估是确定脑死亡受者是否适合接受异种猪器官移植的关键步骤。这一评估的目的是预测和降低移植后可能出现的排斥反应,确保移植器官的长期存活。免疫状态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预存抗体筛查:对受者进行针对猪抗原的预存抗体水平检测,包括抗αGal抗体(针对猪红细胞的天然抗体)和抗非αGal抗原的抗体,高滴度的预存抗体可能增加超急性和急性排斥反应的风险[20]。
(2)交叉配型试验:通过术前交叉配型试验评估受体血清与供体猪器官的免疫兼容性,以预测移植后的急性排斥反应风险。一般采用补体依赖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受体血清与供体淋巴细胞共孵育后,淋巴细胞的杀伤效率不高于20%。
(3)淋巴细胞亚群分析: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受体的T细胞、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亚群,以评估免疫系统的整体状态,建议不超出正常生理值范围。
(4)免疫抑制药物敏感性:评估受体对潜在免疫抑制药物的敏感性,以定制个性化的免疫抑制方案。
(5)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分型:进行HLA分型,以识别可能影响免疫抑制治疗选择和效果的HLA等位基因。
通过上述全面的免疫状态评估,异种移植研究团队能够更好地预测移植后的免疫反应,制定合适的免疫抑制方案,从而提高异种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2.4 社会支持评估
由于脑死亡受者的特殊性,社会支持评估的焦点转移到了其家属或法定代理人身上。因此,需要考察受者家属对于异种移植的理解和接受程度[21],以及家属的决策能力,即其是否具备做出复杂医疗决策的能力,包括理解异种移植试验的潜在风险和社会益处[22]。此外,还应对家属的经济状况、心理健康以及文化和宗教背景进行调查。
3. 法律法规及伦理要求
3.1 法律法规框架
脑死亡异种移植所涉及到的法律框架主要包括3个方面:脑死亡的法律定义、遗体捐赠相关法律和人体试验相关法规。目前,我国尚未从法律层面将脑死亡作为宣布死亡的依据,仅在医学上承认脑死亡[23]。美国则于1981年将脑死亡编入了《统一判定死亡法》(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UDDA)[24]。
遗体捐赠方面,我国于202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中,也仅涉及到了器官捐献的内容,并无捐献脑死亡遗体进行科学研究的相关内容。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的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包括捐献细胞、组织、器官及遗体)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25]。类似的,美国的《统一解剖捐赠法案》(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UAGA)也规定了捐赠过程的法律要求,包括科研用途的遗体捐赠[26]。
人体试验法规方面,目前针对人体受试者的研究[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相应规定及我国的《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已故个体。因此,对于脑死亡受者的研究,同样需要新的指导原则和法规来明确其合法性。
3.2 伦理要求
在脑死亡受者中开展异种器官移植试验,需要在一系列伦理原则的指导下谨慎行事,才能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同时,推动医学研究的进步,为未来器官移植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础。其伦理原则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死者及家属的自主权:进行脑死亡受者的异种器官移植研究时,首要的伦理原则是尊重死者及其家属的自主权。当死者没有留下明确的捐赠或研究意愿时,必须征得家属的同意。这一过程需要详尽的沟通,确保家属充分理解研究的目的、程序以及遗体最终的处置方式。家属的同意不应受到外界压力或不当影响,且他们有权随时撤回同意[17]。
(2)信息透明:研究者必须向家属提供全面、透明的信息,包括试验的具体操作、预期的持续时间、可能的风险和益处,以及遗体的最终归还安排[27]。透明的沟通有助于建立信任,确保家属在整个过程中感到被尊重和理解。
(3)尊重受者尊严:脑死亡受者的尊严和家属的感受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必须得到尊重。研究结束后,遗体应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和归还,以便家属可以根据文化背景和个人信仰进行适当的葬礼和纪念活动。
(4)监督和审查:应当由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研究提案进行审查,确保研究遵循伦理准则[28]。此外,研究过程中的伦理监督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
(5)公众参与和意见:考虑到公众可能对此类研究持有不同的观点,研究者和机构应通过公共论坛、社区会议或媒体发布等方式,积极征求公众意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的透明度,还能促进公众教育,增强公众对器官捐赠和医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促进社会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解和接受[29]。
3.3 动物实验基础
在考虑对脑死亡受者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之前,进行充分的动物实验是至关重要的。为最大程度模拟与人类类似的生理环境,这类动物实验通常需要使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NHP)作为研究对象,如猕猴、狒狒等。
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1)功能性评估,确保移植器官在动物模型中能够执行基本的生物学功能;(2)相互作用分析,研究宿主免疫系统与移植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于理解排斥反应的机制至关重要[30],动物模型也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可能导致免疫激活的特定分子途径;(3)技术优化,改进移植手术的技术步骤,包括血管吻合和器官固定,以及管理排斥反应的策略;(4)安全性评价,在进入人体试验阶段之前,全面了解潜在的风险和并发症,包括对传染病风险的评估[31]。
现阶段进行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的单位需要至少完成5例及以上的猪至NHP实验,且实验中的移植器官类型和亚临床研究的器官类型一致。动物实验数据中,心脏和肾脏移植受者的最长存活时间不低于1个月,肝脏移植受者的最长存活时间不低于2周。
4. 试验终止时间的确定确定
异种器官移植试验的终止时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受者的生理状况、移植器官的功能、排斥反应的风险以及伦理和法律要求等。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试验目的和设计:终止时间首先应由试验的目的和设计决定。例如,如果旨在评估移植后早期的免疫反应,则可能在移植后的几天内终止,建议7~14 d,而如果旨在评估长期移植物存活率,则可能需要延长观察期,建议1~2个月[32]。如果试验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或者达到了预先设定的科学目标,则应当终止试验。
(2)受者的生理状态:需要持续监测受者的生理状态,包括免疫反应、移植物功能和整体生理状况。如果受者出现不可逆的生理或免疫学并发症,可能需要提前终止试验。
(3)伦理考量:根据伦理要求,应避免对受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如果试验导致受者或移植物功能丧失且无法恢复,应考虑终止试验[19]。同时,当伦理委员会认为试验已不再适合继续进行时,也应当终止试验。
(4)风险评估:试验过程中应不断评估与异种移植相关的风险,包括感染风险、免疫介导的损伤和技术上的风险。如果风险超过预期的科学或医学受益,应考虑终止试验[31]。
此外,由于脑死亡受者的特殊性,研究人员应当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情况下,与受者家属共同商定并预先设定终止标准,包括移植成功的标准和因移植物功能丧失而需要终止试验的标准。
5. 家属知情同意制度
知情同意是伦理和法律要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确保了受试者的尊严和选择权得到尊重[33],也反映了国家法律对受试者保护的重视,是进行医学研究的法定前提[34]。在脑死亡受者的异种器官移植中,由于受者无法自行提供同意,其家属或法定代理人的知情同意成为必要条件。为保证受者家属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并为异种移植试验提供伦理和法律依据,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标准化的知情同意文件:应当制定统一的知情同意书模板,明确列出异种移植试验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试验目的、程序、潜在风险及益处。
(2)审核与监管:应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对知情同意过程进行审核,确保同意书的内容全面、透明,并且家属能够充分理解知情同意书上的内容[35]。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也应定期检查和监督异种移植试验的知情同意过程,确保所有规定和指导原则得到遵守[36]。
(3)记录与公证:在家属同意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录音或录像的方式记录同意过程,以证明信息的充分披露和家属的明确同意[37]。或者应有第三方见证人在场,以确保同意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4)定期审查和更新:家属的同意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伦理委员会应定期对同意书进行审查和更新,以适用于试验进展或新的问题。同时,研究人员应当提供专门的教育和咨询会议,帮助家属更好地理解异种移植的相关信息,以及他们的权利和选择[38]。值得注意的是,家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可以随时撤回他们的同意[39],并且这一权利在同意书中应当被明确记录和强调。
(5)透明度报告:研究机构应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公开知情同意过程的相关信息,包括同意书的获取、家属的反馈和任何撤回同意的情况[40]。通过实施这些制度保障措施,可以确保家属的知情同意被妥善记录和监督,从而保护受试者及其家属的权益。
6. 脑死亡判定标准
脑死亡的判定是成功开展脑死亡受者异种移植试验的关键。在制定脑死亡判定标准时,我们综合了国内外广泛认可的《全球脑死亡建议案》(Determination of Brain Death/Death by Neurologic Criteria)[41],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中国人群特点发布的《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42]、《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专家补充意见(2021)》[43]。这些标准为开展脑死亡受者异种移植提供了判定脑死亡的科学依据和操作指南,其要点总结如下。
6.1 判定先决条件在进行脑死亡判定之前,必须确保患者具有明确的昏迷原因,对昏迷原因不明确者不能实施脑死亡判定[42-43],且应当排除可能的混杂因素,如药物效应、代谢紊乱、低温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神经系统的检查结果[41]。
6.2 临床判定标准临床判定脑死亡的标准包括:深昏迷(无对任何刺激的反应)、脑干反射消失(包括瞳孔对光反射、角膜反射、头眼反射等)及无自主呼吸(通过自主呼吸激发试验证实无自主呼吸),且以上3项临床判定标准必须全部符合[42]。
6.3 确认试验标准以下3项确认试验需至少符合2项[42]:(1)脑电图显示电静息状态;(2)正中神经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显示双侧N9和(或)N13存在,P14、N18和N20消失;(3)经颅多普勒超声显示颅内前循环和后循环血流呈振荡波、尖小收缩波或血流信号消失。
6.4 判定次数与人员在满足脑死亡判定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应至少进行3次判定,包括临床判定和确认试验,3次判定间隔不少于6 h。脑死亡判定医师应为从事临床工作5年以上的执业医师(仅限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和麻醉科医师),并且经过规范化脑死亡判定培训。判定时,至少2名临床医师同时在场(其中必须要有至少1名神经科医师),分别进行判定,意见一致时方可认定脑死亡。
7. 小 结
本共识为脑死亡受者的猪肝脏、肾脏、心脏异种移植提供了全面的指导。首先强调了供体猪的基因修饰技术,特别是GGTA1基因敲除,以降低排斥反应风险。同时,受者的选择应当基于严格的生理和免疫状态评估,旨在筛选出最适合移植的个体。在伦理和法律方面,讨论了动物福利、家属知情同意和脑死亡判定标准,确保了研究的合法性和对个体尊严的充分尊重。此外,共识提出了基于受者状况和伦理考量的试验终止时间的确定方法。这些综合措施旨在推动异种移植研究的科学发展,同时维护伦理与法律标准,为临床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略
主审专家:
窦科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郑树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季维智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
薛武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 实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邓绍平 四川省人民医院
编写专家组组长: 窦科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陶开山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编写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陈 凯、陈 刚、代贺龙、戴一凡、丁 睿、杜国盛、冯 浩、冯新顺、伏 志、付迎欣、傅修涛、龚渭华、郝晓军、贺 强、胡 正、季 茹、贾艳艳、赖良学、李 民、李巅远、李 琳、栗光明、龙恩武、门同义、潘登科、彭 江、秦卫军、曲 伟、师长宏、司中洲、宋文杰、陶开山、王 峰、王 琳、王 维、王 毅、卫 强、魏红江、熊韫祎、杨 卿、杨宏伟、杨欣荣、杨永广、杨诏旭、杨雁灵、殷 浩、曾 仲、张 玄、张雷达、张全保、张洪涛、张若涵、章忠强、周 亮
执笔作者: 窦科峰、陶开山、张 玄、宋俊伯
【引用本文】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异种移植学组. 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专家共识(2024版)[J]. 器官移植, 2024,15(5):653-660.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4212.

 扫一扫
扫一扫